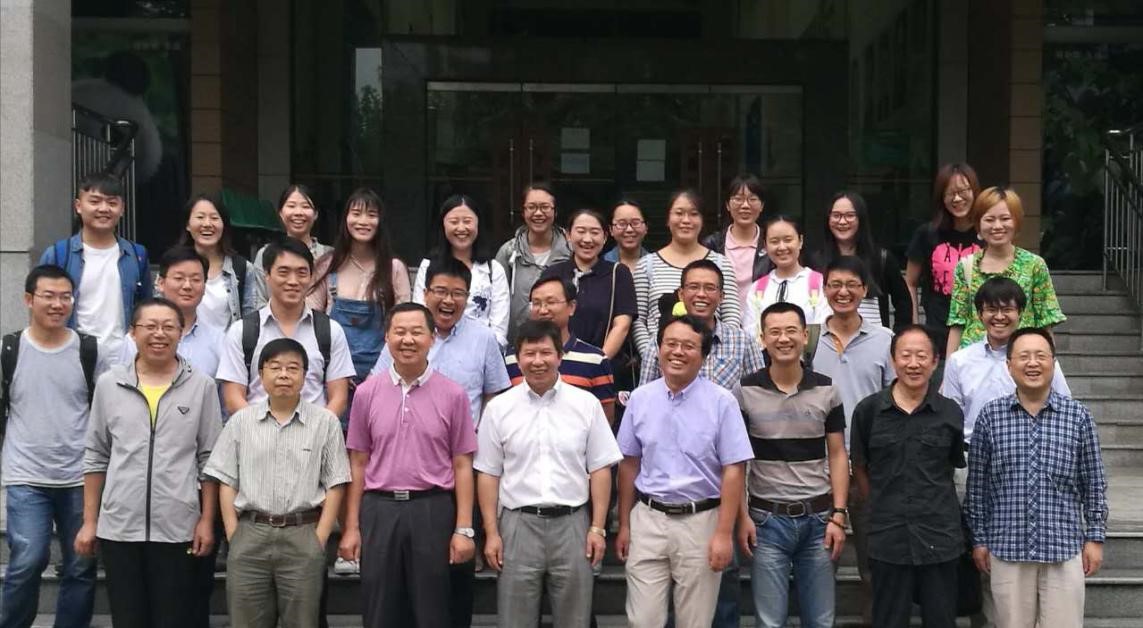手工业考古专题沙龙(第一期)——矿冶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纪要
发布日期:2017-09-27 作者:管理员来源:
2017年9月16日,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手工业考古沙龙”第一期——“矿冶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在66668银河国际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的主讲嘉宾有:陈树祥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延祥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陈建立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莫林恒副研究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映福教授(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吕红亮教授(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黎海超讲师(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刘芳博士(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参与沙龙讨论的还有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省铸造学会、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和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66668银河国际制造学院、66668银河国际材料学院的师生。
李映福教授首先介绍了考古学系主办沙龙的缘起。学术沙龙因规模小,研讨题目清晰明确而日益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学术交流方式。冶金手工业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近年来的新发现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日益受到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从2015年首项社科重大项目立项到2017年度的四项重大项目选题,可以看出深入开展冶金手工业考古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66668银河国际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举办“冶金手工业考古系列沙龙”就是希望创建一个持续交流冶金手工业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平台,同时又能为我校师生提供学习、研究的机会。
陈树祥研究员的《走进铜绿山》分五个方面报告了铜绿山遗址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及其价值、影响。考古新发现主要包括岩阴山脚遗址洗选矿的尾矿堆积、选矿场、足迹、探矿井,四方塘遗址的冶炼渣、冶炼炉、焙烧炉及墓地等。与铜矿冶密切相关的墓地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发掘者借助遗迹与遗物的关联性,推测墓葬主人的身份可分矿冶管理者、保卫者、生产者等几类。遗址内各区域的研究可还原春秋时期矿冶生产中的功能分区,对文化因素的细致分析,大致认定楚人经略铜绿山的时间、楚文化和扬越文化的融合特征,一些新的发现还有助于研究铜绿山与商周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曾国、楚国与铜绿山矿冶的关系。陈树祥与李延祥、陈建立教授建立了长期科研合作,通过对四方塘遗址出土炉渣成分的检测和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分析,推测铜绿山当时的冶炼水平和铜料流向,认为春秋时期的冶炼水平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此外,通过梳理以往铜绿山发掘材料并结合新的发现,对铜绿山的始采年代认识有了新的线索,即初步推断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宋、明、清焙烧炉的发现也为研究硫化铜矿冶炼前脱硫处理提供了大量新资料,填补了古代文献的空白。陈树祥研究员报告中还展示了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宏伟建设规划,令人兴奋。
莫林恒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古代炼锌作坊的完整揭示》。报告者以一段古代炼锌技术的复原视频为引,详细报告了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的发掘收获与认识。该项目是由湖南省考古所和北京大学陈建立老师的研究团队共同开展的。2016年对十四处炼锌遗址进行了专项调查,发现冶炼遗址中冶炼场位于煤矿附近,由于冶炼中需要的煤量大于所需的矿量,因此需要将矿石运至有煤的区域进行冶炼,形成了“以矿就煤”的分布模式;冶炼遗址大多分布在山丘平坦开阔的区域,发掘中对矿渣堆积的冶炼平台进行了整体揭露。发掘之初进行了虚拟布方,将发掘区分为三个区域,分别对应三个冶炼单元。焙烧区发现了六条焙烧炉,每条有四个或者八个炉体。冶炼作坊以冶炼炉为核心,周围分布着各类相关遗迹。储料坑一大一小,用于堆放矿和煤混合的原料。废料坑一高一低,分别堆放铜渣和铅渣。另发现有数排柱洞,分布有规律、推测应为炉棚。
莫林恒先生还介绍了相关生产流程复原、科技分析工作。经检测,发现的矿石主要为锌矿、铅矿,经过筛选、分开冶炼;对坩埚中炉渣的分析,发现主要为硫化锌矿,少量为氧化锌。后者不需要焙烧,直接入罐冶炼。炉渣内发现有铅冰铜,印证了桂阳史料中记载的以铅渣提炼铜的技术。此次发现的焙烧炉、冶炼炉、精炼炉,属于产业流程完整、技术完备的炼锌作坊,在聚落考古、工艺流程、生产者研究等多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最后莫林恒先生简要比较了桂阳与重庆两地炼锌技术的异同,并就现阶段冶金考古的发展现状与诸位学者进行讨论。
黎海超博士以《技术、文化与人群—铜岭与铜绿山遗址新论》为题做报告。黎海超认为对矿冶遗址的理解应是立体的、综合性的,可概括为技术、文化与人群三个层面。其中技术层面包括采矿、冶炼等过程的一系列技术环节,文化层面涉及陶器群的面貌以及聚落形态等方面,人群则主要指矿冶遗址中生产者的族属、等级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等等。只有从不同层次深入分析矿冶遗址,才能构建起对矿冶遗址的全面认识,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
铜岭和铜绿山遗址经早年发掘备受学界关注,但对于两遗址的关系仍缺乏详细讨论。为此,黎海超以铜岭和铜绿山为例,从生产技术和陶器群面貌两个方面,分时期对两个遗址进行系统对比。认为在商周时期南北资源、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阐释两个遗址所扮演的角色当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视角。
黎海超认为铜岭遗址与铜绿山遗址所采用的技术体系在诸多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如铜岭的井巷支护结构惯用“碗口接”式连接技术,而铜绿山则始终流行榫卯式技术。但西周时期两遗址出现技术系统的“趋同性”,短暂的趋势到了两周之际前后又戛然而止,春秋时期两地恢复到各自的传统技术体系中。与这种技术体系的改变相应的是两地陶器群面貌的变化。铜绿山遗址地处鄂东南,该区域属于大路铺文化的分布范围。铜岭遗址在不同时期可见有本地文化因素和商文化等外来因素的共存。值得注意的是铜岭遗址在西周时期出现大路铺文化因素,春秋时期又可能为楚文化因素替代。也就是说,控制铜绿山所在区域的大路铺文化在西周时期当向东扩张至铜岭遗址,这或是铜岭和铜绿山在西周时期出现技术“趋同性”的原因所在。春秋时期,随着大路铺文化的退缩,两地又恢复至原本的技术体系。直到战国至西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大部分矿冶遗址可能均归于楚的控制。
最后,黎海超结合上述分析结果,联系到楚公逆钟及晋姜鼎的铭文记载,进行了一些科技分析,将考古、铭文、科技分析综合起来复原了大路铺文化至楚再至晋的铜料流通过程。
刘芳博士以《武陵山区朱砂矿冶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主要介绍了自2016至今武陵山区朱砂矿冶遗址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通过对朱砂开采、水银冶炼遗址和相关聚落、墓葬、古驿道等遗存来梳理手工业生产体系,讨论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刘芳博士分别报告了贵州务川、万山两个调查区域内矿洞、聚落、墓葬、古城墙、码头、古驿道等考古成果及其认识。务川、铜仁两地作为贵州乃至武陵山区朱砂资源开发的核心区,其开采时间自秦汉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矿山规模及采掘面积大,是目前我国保存较好的矿冶了简要介绍,根据考古发现同时开展了火爆法采矿等模拟实验。
武陵山区内各时期遗址的分布与矿山、资源、运输线路密切相关,矿产资源的兴盛枯竭是该区域社会发展的核心。各类遗址的发现,极大丰富了贵州地区手工业考古的基础资料。武陵山区历史时期内必然存在着一条以朱砂和汞流通为媒介的“朱砂通道”,朱砂既是这一通道主要往来的贸易物品,也是承担诸多交流因素的物质载体,乌江流域既是寻求朱砂资源之路,也是汉代中原文化进入贵州所经的重要通道,沅水流域则承担起唐宋至明清时期连接武陵山区和东部长江流域的通道作用,因此,可将这条“朱砂通道”视为“文化输入、产品输出”的交流通道,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国西南地区而言,有着与古代丝绸之路同样深远而非凡的意义。
最后,刘芳博士认为根据调查所见的遗迹、遗物,对这一区域的调查研究应涉及手工业考古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采矿技术与生产流程、产品研究、流通与应用、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与布局、社会经济文化研究等多项研究内容,需在科学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手工业考古的视角综合观察问题。
李延祥教授以《中国四个地区的早期青铜矿冶遗址考察与研究》为题,主要介绍晋南、河西、辽西以及长江中下游四个区域内(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青铜矿冶遗址的考古发现情况。
晋南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龙山至二里岗阶段的冶炼遗址7处。其中,刘家庄遗址出现少量炼砷铜炉渣,年代可能为龙山晚期,其余各遗址皆为由氧化矿石直接冶炼红铜的遗址,未见任何进一步炼制砷青铜、锡青铜的证据。
河西地区有西城驿、火石梁等10处遗址。该区域绝大部分炉渣皆为使用氧化矿石冶炼铜的炉渣,但部分渣中出现有含砷、锡、铅、铋、锑的青铜颗粒,检测到共生有锡、砷、铅的矿石。二道梁、一个窝地南、西土沟、土西沟以冶炼砷铜为主,西城驿、火石梁、缸缸洼既有砷铜,也有锡青铜。砷铜的冶炼引入了砷氧化矿物及铅砷矿等含砷矿物。火石梁、缸缸洼两遗址发现的含锡矿石与一般氧化矿石不同源,为寻找锡料来源奠定了基础。张掖西城驿、火石梁、缸缸洼、二道梁、一个窝地南遗址、西土沟等冶炼遗址年代较早,白山堂采矿遗址和古董滩冶炼遗址年代较晚。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有大甸子、牛河梁炼铜遗址群等,青铜时代晚期有大井古铜矿、敖汉旗周家地冶炼遗址等。辽西青铜时代晚期是铜锡砷共生矿冶炼。塔布敖包等11处冶炼遗址的矿料来源于大井古铜矿,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上窑遗址和周家地遗址矿料来源不是大井古铜矿,它们不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应是新的考古学文化(井沟子类型),年代晚到战国晚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皖江流域、九江地区早期矿冶遗址考察(含冶铸遗物),共调查遗址及矿山227处。
李延祥教授总结了不同区域青铜器产业的格局,发现普遍存在采矿、冶炼遗址分离,采矿在山、冶炼近水,依托河流为通道,以石器采矿,冶炼遗址精心选择等共性。四个区域早期冶金遗址的内涵与格局各有差异的特性。中原晋南呈现分级现象,冶炼遗址仅冶炼纯铜,只有在垣曲商城、东下冯遗址出现青铜铸造遗址。虽然目前仅初步探明铜的产业链,但一定存在未发现的锡铅的产业链,铜的产业链与锡铅产业链只在最高级的二里头遗址和次高级的东下冯等遗址才能连接在一起。辽西青铜时代早期可能与中原相近。河西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锡砷等资源直接在与炼铜遗址相结合的现象,没能出现明显的分级。但长江中游地区有容器的铸造。辽西青铜时代晚期由于资源方面的优越性,反而未能出现冶金遗址的分级,多处遗址内涵相同,无等级差别。
陈建立教授以《矿冶遗址的研究、保护与展示之所思》为题,结合近年来开展的田野工作,围绕冶金遗址的研究、保护、展示等问题进行讨论。
陈建立教授认为冶金考古中需要研究的是包括矿产、采矿、冶炼、铸造等的整个过程,需要结合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在进行冶金遗址调查时,不仅应关注遗址,同时要观察废弃物、关注遗址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结合文献方志等材料,不同区域要寻求适合当地的特色方法,同时不能忽视对矿洞、矿物流通、采冶者的研究。若对难以判断性质的堆积、遗存存疑问,可以借助实验考古解决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连续两年组织开展冶金实验考古,为教研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实验考古开始前,要对周围环境做检测,了解重金属含量、分布等信息,结束后还要对冶炼垃圾进行掩埋并及时跟进相关采样研究工作。
谈到遗址保护时,陈建立教授感叹虽然我国矿冶遗址数量众多,但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却少之又少,铜绿山、万山汞矿等遗址的保护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不仅缺乏专门的保护机构和人员,同时也缺乏较好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另外,矿冶遗址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由此,他强调既要加强研究,也要做好遗址的价值评估和合理规划,进行科学、实际的保护。除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应加强推广及成果展示工作,通过视频公开课、纪录片、展览等形式,让公众了解矿冶遗址及其价值。
近年来陈建立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持续关注资源与环境、技术与文明、中原和边疆的关系,以及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商周时期北方和南方资源等重要学术问题,通过此次沙龙,他希望跟各位学者继续开展合作,最后他再次强调:应通过多学科融合促进研究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在保护还是研究中都应以宏观的视角观察问题,由单个遗址扩展到整个流通或技术范围内,将研究重点由单一的冶金技术扩充为涵盖生产者及社会等方面。
李映福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金属矿产与冶金技术的传播》。报告者梳理了“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金属矿产资源的文献记载和秦汉以前的金属产品与冶金遗址的空间分布,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存在着中原的竖炉冶金技术与“碗式”炉冶金技术及其产品。
“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延续和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秦汉时期,随着以成都平原为前进基地的冶炼技术的扩散与产品的流通,形成了“生铁”与“块炼铁”冶铁技术、产品共存的格局。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越嶲郡(凉山西昌)是两大技术体系的重要分界点,以北的地区为“生铁系”区域,以南则存在“块炼铁系”的冶金技术及产品,其形成与汉代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有关。块炼铁冶金技术与产品的分布范围主要在“西南夷”系统的区域,其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东南亚有密切联系。“生铁系”冶炼技术与产品的扩散是促进“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及西南夷地区社会分化 →瓦解 → 重组 → 汉化的主要动力。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以“资源、技术、社会”的视角,观察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金属器物形态,进而解读器物形态变化的内在机理。
吕红亮教授发言题为《围观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之争》,吕红亮教授阐述了目前学界围绕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问题的争论,通过对老挝Sepon矿区冶铜遗址田野调查情况的介绍,探讨了Sepon冶铜遗址对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的争论以及西南地区冶铜技术研究的意义。东南亚冶金考古尤其是青铜技术起源是70年代至今的热点问题,近些年学术界对于中国起源论获得了共识,但对于具体路线却存在激烈的争论。主持发掘班清遗址的Joyce White认为东南亚最早的冶铜技术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由中国西北地区通过西南山地进入东南亚的,东南亚早期青铜器跟齐家以及欧亚草原冶金系统(塞伊玛-图尔宾诺)有关。另外一种意见以Charles Higham为代表,主张东南亚冶金技术是中原系统通过东南沿海的岭南地区进入东南亚的。
吕红亮教授通过梳理考古材料,对比了东南亚与中原地区冶金技术传统的异同,指出东南亚可能有其独特的冶金技术,分别表现在简单合范的使用、青铜产品的小型化、碗式坩埚主导、铜锭生产与流通等,上述特点在中国西南山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里也很常见。目前为止东南亚采矿、冶炼、铸造可形成冶铜链条的有三个区域,一是泰国东北部Phu Lon,年代可早至公元前第一千纪,持续至100.BC,该冶炼遗址发现有石锤、竖井、坩埚和模范,属于季节性冶炼遗址,附近聚落少;二是泰国中部的Khao Wong Prachan流域的诸遗址,年代为1000.BC至500.AD,发现有采矿、坩埚、炉具和成吨的矿渣;三是新发现的老挝南部的沙瓦纳吉省(Densavan)的Sepon矿区,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铜矿区。
Sepon矿区矿山面积很大,发现了四处相距不远的遗址,分别是Peun Baolo(遗址的名字就是“坩埚地”)、Dragon Field、Khanong A2和Tengkham South D。其中Khanong A2和Tengkham South D属于现代开采区,发现有大量竖井,Tengkham South D还发现了疑似船棺葬的木船。另Peun Baolo发现了墓葬,出土了不少装饰品和铜锭。Dragon Field年代稍微晚一点,发现了大量的装饰品和青铜容器。通过对四处遗址发现的遗物进行测年,发现数据基本都在距今2000年左右。
通过Sepon矿区和其他区域的研究来看,在东南亚早期冶铜生产中看不到社会复杂化倾向。从铅同位素上来看,整个东南亚的青铜器的贸易流通非常复杂,虽然在Sepon矿区发现的很多遗物的矿源属于本地区,但也有来自泰国东部和北部的矿源。泰国中部地区的矿源更加复杂,有Sepon矿区、泰国北部和越南北部。这可能体现出了一个范围很大的青铜贸易网络。另外从采矿的矿井来看,可以看到同铜绿山有高度相似性,但从年代上来看,又比铜绿山早期阶段晚了很多,属于战国至汉时期,因此很有可能铜绿山技术体系对其有很大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有非常密集的年代学数据积累,已经可以明确最早的冶铜产品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但西南地区却无法如此确定。如果要进一步回答东南亚地区冶铜起源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国西南地区考古学研究基础的薄弱,迄今没有确切的开采、冶炼、铸造遗址,年代学体系依然相当粗糙。例如海门口遗址出土了被认为是西南山地最早的青铜器,但关于年代却仍存在争议。
另外,在研究思想上,也需要考虑更复杂的情况,今天我们是否将古代青铜采矿、冶炼、消费和流通的情况思考的过于简单,是否存在一个早期跨东南亚大陆的金属交换体系仍需进一步讨论。
沙龙的自由讨论环节由黎海超讲师主持,诸位学者就矿冶遗址调查和发掘的工作方法、矿冶考古研究方法(如商周时期与历史时期矿冶遗址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矿冶考古的现存问题及未来的研究重点三个主题进行热烈讨论。
李延祥教授认为矿冶考古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就四川地区来看首要任务是解决三星堆冶金技术的相关问题,三星堆拥有其独立的青铜生产区,铸铜作坊一定在三星堆文化的某个遗址当中,建议在工作中寻找标志性冶金遗物,如石锤、炉渣、矿石、鼓风管等。四川盆地同甘青地区联系密切,应将两个区域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除铜器外,对铁器及冶铁遗址的研究也需要注意一些关键问题,借助对考古发现炉渣的科学分析检测,区分块炼铁炉和炒钢炉等。
针对李延祥教授的发言,李映福教授介绍了三星堆目前的研究情况,提到距三星堆不远的四川彭州发现有许多矿洞,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早年有学者考察过其矿藏的分布为玉-铜-金的立体分布形式,但由于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地质条件不稳定,频繁地震后地质地貌发生较大改变,不便于深入开展工作。
陈建立教授在讨论中提到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冶金考古工作离不开田野,检测分析及研究时一定要将采集的标本还原至考古背景中;研究应当围绕资源与社会、技术与人文、中原与边疆等主题方面展开;应逐步建立实验室数据标准并开展数据库的建设,目前国内的相关工作较为薄弱。他还以牛津大学提出的“牛津研究体系”为例,提醒研究者们在借鉴国外理论方法时,一定要注意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研究不能只关注技术层面,还要从田野的微观入手,开展多层面的研究。
与会专家针对矿冶考古的诸多方面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李映福教授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种形式轻松、讨论自由、问题明确的小型沙龙对于对冶金考古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最前沿的考古理论与方法,还可以为后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对下一步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向作用。最后,李映福教授再次对与会学者及嘉宾表达感谢,首期手工业考古专题沙龙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